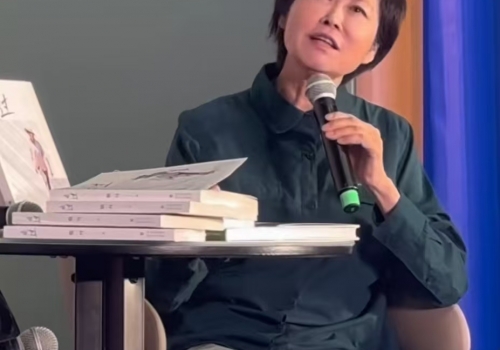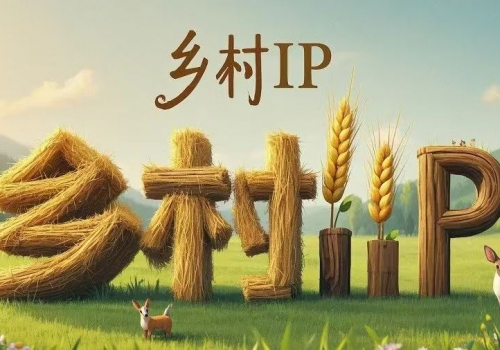平凉文旅困局,从崆峒山失语到管理失能的系统性危机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,平凉坐拥崆峒山这一道教圣地的5A级景区,却在2024年文旅消费升级浪潮中陷入尴尬境地——崆峒山景区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00万人次,但人均消费仅68元,远低于全国山岳型景区156元的平均水平;斥资12亿元打造的崆峒小镇,商铺空置率高达45%,夜间亮灯率不足三成。这种“流量虚胖、效益贫血”的困境,折射出中国西部文旅转型中的深层矛盾。
一、资源诅咒:崆峒山的失语与异化
崆峒山的困境始于“文化空心化”。作为道教发源地,其核心吸引力本应是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体验,但现实开发却陷入三重误区:景观同质化:景区将80%的改造资金用于玻璃栈道、高空滑索等“网红标配”,与武当山、三清山等形成同质竞争,丧失了“问道崆峒”的独特性;
文化符号滥用:黄帝问道广成子的典故被简化为雕塑群与表演秀,游客服务中心售卖“崆峒仙丹”实为普通养生茶,道教文化的深度阐释让位于快餐式消费;
生态承载失控:景区最大承载量2.5万人/天,但在旅游旺季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,导致古建筑群地基沉降、千年柏树根系受损等生态危机。崆峒小镇的失败更具警示意义。这个规划中的“文旅综合体”,因管理失序沦为“空壳工程”:
业态错配:商铺招商中火锅店、密室逃脱占比超60%,与“道文化小镇”定位严重偏离;
运营脱节:政府主导的“平凉文旅集团”缺乏市场化经验,商铺租金高于周边商圈30%,却未配套引流措施;
文化失血:原住民搬迁后,传统庙会、社火等活态文化消失,仿古建筑沦为拍照背景。
二、管理失能:体制性梗阻的解剖
平凉文旅部门的治理困境体现在三个维度:多头管理痼疾,崆峒山景区涉及宗教、文物、林业等7个管理部门,崆峒小镇开发由住建、文旅、城投等多方主导。这种“九龙治水”格局导致 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冲突(如道观厢房被改为民宿引发争议); 跨部门数据壁垒(游客消费数据无法与交通、商业部门共享); 应急响应迟缓(2023年暴雨致山体滑坡,因责任归属争议延误救援2小时)。
政策执行悖论,尽管市级文件要求“强化文化IP打造”,但执行中异化为形式主义: 耗资千万的“崆峒文化研究院”沦为接待中心,三年仅产出2篇学术论文; “百万创意征集计划”中87%获奖方案因部门利益纠葛未能落地。
人才机制僵化,文旅系统存在“三低现象”,专业人才占比低(全市文旅系统本科以上学历者仅39%); 薪酬竞争力低(基层员工月薪比兰州同行低32%); 创新容错度低(某科长因引入VR导览设备故障被问责,导致新技术应用停滞)。
三、消费代差:供需错位的市场惩罚
平凉的困境本质上是传统文旅模式与新生代消费需求的断裂:体验经济缺位,年轻客群期待的“沉浸式问道之旅”尚未开发,现有产品仍停留在登山观光层面。对比武当山“太极晨练+道医问诊+《梦幻武当》演艺”的全链条体验,崆峒山的文化变现能力落后一个代际。
夜间经济塌陷,崆峒小镇夜间仅有路灯照明,缺乏“夜游崆峒”产品设计,而同期重庆洪崖洞夜间消费占比达全天营收的68%。文旅部门规划的“星空露营”项目因安全审批拖延三年未实施。二次消费乏力,景区70%收入依赖门票,文创产品开发停留在“贴标阶段”(如印有崆峒山logo的普通保温杯),与敦煌“飞天盲盒”年销过亿形成鲜明对比。
四、破局路径:从管理革命到价值重构
体制层面成立“崆峒山文旅特区”,赋予其规划、招商、执法等综合权限,终结多头管理; 建立“文旅创新容错清单”,允许试错性改革(如引入社会资本开发悬崖酒店)。
开发“问道十二时辰”沉浸式体验,将晨钟暮鼓、道教斋醮转化为可参与仪式; 打造“崆峒武学”IP,与少林寺、武当山形成差异化竞争。 对崆峒小镇实施“业态重置”,引入非遗工坊、道文化书店等主题空间,空置商铺改造为研学基地; 推行“消费积分制”,游客在景区餐饮、住宿消费可抵扣二次项目费用。
唤醒沉睡的文化基因。
当崆峒山的云雾依旧缭绕,当崆峒小镇的灯笼在夜风中孤悬,平凉文旅需要的不仅是硬件升级,更是一场从思维到制度的深层变革。唯有将文化敬畏注入管理血脉,用市场逻辑重构产品体系,方能在“流量泡沫”中锻造出真正的文旅竞争力。
这座千年古城能否破茧重生,取决于管理者是否有勇气打破既得利益藩篱,让崆峒之道真正“道法自然”。(作者:介一)